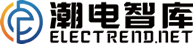在中美貿(mào)易爭端,英國脫歐和歐美貿(mào)易爭端的影響下,全球供應(yīng)鏈重構(gòu)越來越為國際資本所重視,如何吸引資本關(guān)注,以維護(hù)或提振自己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成了工業(yè)國家與地區(qū)政府的重要任務(wù)。
與中國推動制造2025,美國推動美國制造回流,歐盟推動工業(yè)4.0等不同,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國家,由于目前的現(xiàn)狀下,工業(yè)體系完整度較低,幾乎沒有能力實現(xiàn)自己的產(chǎn)業(yè)升級,尋找聯(lián)盟對象組團(tuán)打怪,成了這些國家或地區(qū)的一種合理應(yīng)對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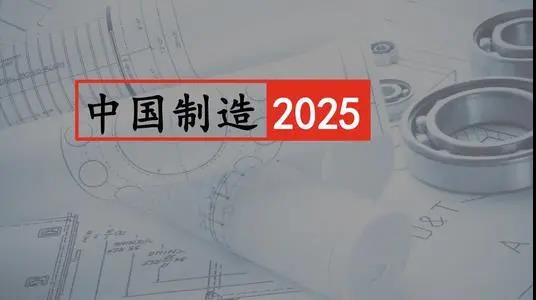
圖/網(wǎng)絡(luò)
如此次會談結(jié)束后三國部長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中顯示,由于新冠疫情導(dǎo)致以制造業(yè)為中心的多個行業(yè)供給停滯,聲明強(qiáng)調(diào)了“強(qiáng)化產(chǎn)業(yè)鏈的必要性”。同時,聲明還明確呼吁東盟成員國等其他國家加入。
有分析人士認(rèn)為,日、澳、印三國聯(lián)手,主要是因為各有所長,可實現(xiàn)良好的互補(bǔ)。日本制造業(yè)擁有雄厚的技術(shù)實力,但是資源匱乏、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進(jìn)程遲緩,希望從稀有金屬等資源豐富的澳大利亞和信息技術(shù)人才眾多的印度借力。而擁有巨大國內(nèi)市場的印度可以借助同日、澳的合作加速建設(shè)其并不完善的道路和港口等基礎(chǔ)設(shè)施。
這三個國家里面,日本雖然企業(yè)實力強(qiáng)大,但由于日本國土面積和市場空間較小,所以日本企業(yè)在海外擁有很多的生產(chǎn)基地。此次疫情發(fā)生后,事實上日本政府已經(jīng)考慮在日本國內(nèi)建立最低限度的工業(yè)制造體系。
特別是在與民生與國家發(fā)展相關(guān)的基礎(chǔ)生產(chǎn)、生活物質(zhì)領(lǐng)域,日本已經(jīng)通過向全社會募集資金,讓這些企業(yè)把一些處于海外敏感國家或地區(qū)的生產(chǎn)產(chǎn)能,能部分或全部遷回日本國內(nèi),對于嚴(yán)重依賴勞動力或消費市場的物質(zhì)供應(yīng)鏈,則可以考慮遷往東南亞日本制造業(yè)傳統(tǒng)可控的國家或地區(qū)。
從日、澳、印三方這個聯(lián)盟來看,很明顯的就是針對如何支解中國制造制定的,希望在全球供應(yīng)鏈體系中的降低對中國制造的依賴。
事實上,在國際資本市場上,蘋果的動作也側(cè)面證實了全球供應(yīng)鏈對中國制造風(fēng)險意識在增強(qiáng),特別是在中美貿(mào)易糾紛看不到終點之際。
近十年來,中國以較完整工業(yè)體系的優(yōu)勢,把全球的制造業(yè)產(chǎn)能大部分復(fù)制到了中國內(nèi)地,而且由于產(chǎn)能擴(kuò)張迅速,中國制造所引起的產(chǎn)能過剩,也讓全球的商品價格戰(zhàn)也無法停止下來,多少大宗消費品商品都只能綁在中國制造這輛不知何時才會停止的戰(zhàn)車上。
如果說中美貿(mào)易是由于雙方的貿(mào)易逆差,以及知識產(chǎn)權(quán)稅無法對中國收取導(dǎo)致美方利益受損,導(dǎo)致雙方長期以來的貿(mào)易摩擦不斷,那么日本、澳大利亞、印度三方又是抱著什么態(tài)度,要來從支解中國制造中分一杯羹呢?

圖/網(wǎng)絡(luò)
其實日本和澳大利亞在全球供應(yīng)鏈中并沒有多少訴求,因為日本是全球制造業(yè)的基礎(chǔ)設(shè)備及設(shè)備元件供應(yīng)商,澳大利亞在全球供應(yīng)鏈中,更多的只是充當(dāng)原材料粗礦供應(yīng)商角色。
對于這兩個國家來說,全球供應(yīng)鏈重構(gòu)所產(chǎn)生的制造產(chǎn)能重復(fù)建設(shè),只會加大市場對它們的需求,比如現(xiàn)在印度正在全力從中國內(nèi)地爭搶制造業(yè)產(chǎn)能配置時所產(chǎn)生的需求。
所以從根本上來講,這一次的聯(lián)盟應(yīng)該是印度以市場需求來組建的一個全球供應(yīng)鏈重構(gòu)局部循環(huán)體系,由于印度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不確定性,與技術(shù)人才的缺陷性,所以還需要東盟這些東南亞國家給圈進(jìn)來,才能完成復(fù)制出一個類似中國內(nèi)地那么完整的工業(yè)體系出來。
如果無法在一個單一市場上,復(fù)制出一個類似中國內(nèi)地那么完整工業(yè)體系的制造業(yè)產(chǎn)能基地出來,實際上未來一段時間內(nèi),全球供應(yīng)鏈體系中,中國制造還是無法一個難以回避的商業(yè)難題。
印度在今年上半年對全球資本投資在中國內(nèi)地的上千家企業(yè)進(jìn)行了調(diào)研,并對這些企業(yè)發(fā)出了前往印度投資的邀請。為了實現(xiàn)這些企業(yè)可以在印度落地,印度政府今年上半年出臺了相對激進(jìn)的制造業(yè)刺激政策,來扶持國際資本在印度配置產(chǎn)能。
但是全球的資本市場并不完全相信印度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把中國內(nèi)地的產(chǎn)能復(fù)制過去,特別是對工程師人數(shù)要求較多的零組件加工段,印度明顯工程師數(shù)量不足。
而中國近十年的制造業(yè)大發(fā)展,除了有大量原來的外資或合資企業(yè)培養(yǎng)出來的大量熟手員工、技術(shù)人員、工程師與管理人員充實到各個行業(yè)以外,中國內(nèi)地前二十多年的院校擴(kuò)招,也為中國內(nèi)地的制造業(yè)輸送了海量工程師隊伍。
不客氣的說,中國內(nèi)地近十年依賴工程師紅利,幾乎讓中國內(nèi)地制造業(yè)產(chǎn)值翻了幾番,相關(guān)企業(yè)在股市上的市值也同樣翻了數(shù)番。
但印度目前顯然在熟手員工、技術(shù)人員方便有所欠缺,而印度大量的工程師人才,都是偏向管理階層和數(shù)字軟件人才,對于實體制造業(yè)的工科技術(shù)人員,數(shù)量上還是沒了中國內(nèi)地多。
因此印度目前正在吸引的是對勞動力人員數(shù)量較多的后段組裝部分,以及前段自動化較高的原材料加工部分。
那么現(xiàn)在日本和澳大利亞能不能短時間內(nèi)補(bǔ)全中國內(nèi)地的零組件加工部分呢,看起來也比較困難。
澳大利亞仍然只希望出口原材料,它與印度和日本結(jié)盟的主要原因,也就是繼續(xù)保住自己的市場份額,希望中國內(nèi)地減少進(jìn)口的部分,印度和日本能夠快速填補(bǔ)上來,要澳大利亞自己建造類似中國制造的大加工產(chǎn)業(yè),澳大利亞同樣缺乏相應(yīng)的人才。
日本更不用說,日本如果有能力完成這部分產(chǎn)能在日本本土完成,也就不會出現(xiàn)日本經(jīng)濟(jì)泡沫,經(jīng)濟(jì)發(fā)展幾乎停滯了二十多年。
所以日本提出的方案,就是以東南亞來彌補(bǔ)零組件加工部分。
東南亞有著同樣多的人口,并且也有很多西方大學(xué)培養(yǎng)出來的工程師人才,還在三十年前受益亞洲四小龍的經(jīng)濟(jì)騰飛溢出紅利,形成了部分零組件的加工產(chǎn)能基地與技術(shù)儲備,只需按部就班擴(kuò)大產(chǎn)能,就能替代掉部分中國內(nèi)地的制造產(chǎn)能。
在這一次貿(mào)易糾紛政治化后,其實不僅海外資本對中國內(nèi)地的產(chǎn)業(yè)政策抱有戒心,正在把與中國內(nèi)地迅速增長的相同制造業(yè)環(huán)節(jié)產(chǎn)能出清,要么關(guān)停,轉(zhuǎn)移到其它區(qū)域,如三星的手機(jī)、電腦、電視制造轉(zhuǎn)移到越南和印度;要么把產(chǎn)能轉(zhuǎn)賣給中國內(nèi)地廠商,如三星的面板、高偉的攝像頭、可成的機(jī)殼加工等。
即便是在全球產(chǎn)業(yè)鏈中占據(jù)重要地位的臺灣,目前也難以讓海外資本放心。在國際資本的推動下,實際上終端廠商也要求臺灣廠商在海外尋找新的產(chǎn)能基地,包括南向東南亞,甚至轉(zhuǎn)往拉美或東歐地區(qū)。
從目前全球供應(yīng)鏈格局來看,政局穩(wěn)定,又有意愿接收制造業(yè)轉(zhuǎn)移的地區(qū)確實難找。

圖/網(wǎng)絡(luò)
前面說的印度,有著與中國類似的國情,但是其引以為豪的社會制度,其實很難與類似計劃經(jīng)濟(jì)的大制造業(yè)相匹配。除非印度也對制造業(yè)元素采取類似計劃經(jīng)濟(jì)分配制,重新進(jìn)行強(qiáng)勢管制。
而拉美雖然是歐洲的表親,但多年的軍閥管制,同樣讓制造業(yè)元素?zé)o法按市場規(guī)律進(jìn)行,甚至出現(xiàn)了難民北逃美國的局面。
東歐地域太小,格局也太小,雖然在單個領(lǐng)域,東歐經(jīng)常能出現(xiàn)領(lǐng)先全球的技術(shù)出現(xiàn),但對于大制造業(yè)這種系統(tǒng)工程,東歐同樣還要一個過程來統(tǒng)合。
所以國際資本只能把大制造產(chǎn)能雞蛋分別往印度、東南亞、東歐分散,每個籃子里都撒下種子,即讓它們與中國內(nèi)地競爭,也讓它們各自競爭。最后各憑本事,瓜分產(chǎn)能。
事實上,美國也在努力平復(fù)中東的亂局。美國正在要求以色列周邊的國家站隊,要么站在美國一方,拿到全球資本市場入門券,要么承受西方資本市場的全力封鎖,讓你自生自滅。
美國除了希望能在中東也打造出一個大制造業(yè)基地出來外,把中東作為東西方意識形態(tài)的緩沖地,也是美國智庫的一種打算。西方資本希望中美如果出現(xiàn)徹底脫鉤現(xiàn)象,以以色列為首的中東地帶,以及原來的中歐市場,還可以讓東西方互通有無,減少未來制造業(yè)貿(mào)易雙軌制運行后產(chǎn)生的兼容性成本。
全球產(chǎn)業(yè)鏈重構(gòu),供應(yīng)鏈再造已經(jīng)勢在必行,這不僅是全球貿(mào)易戰(zhàn)的需要,也是中國內(nèi)地發(fā)展的需要,否則也就不會有中國的“一帶一路”,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實際上就是中國自己主動尋找第三方國家或地區(qū)來承接中國內(nèi)地制造業(yè)轉(zhuǎn)移。
只是中國的全產(chǎn)業(yè)鏈擴(kuò)張模式,讓全球資本少了主動參與的機(jī)會,所以才會出現(xiàn)美國制造業(yè)回歸,與日、印、澳供應(yīng)鏈同盟出現(xiàn)。
說到底,其實沒有所謂的支解中國制造業(yè)這回事,一切的動作都是在爭取全球制造業(yè)產(chǎn)能的話語權(quán),包括產(chǎn)能基地全球配制話語權(quán)。